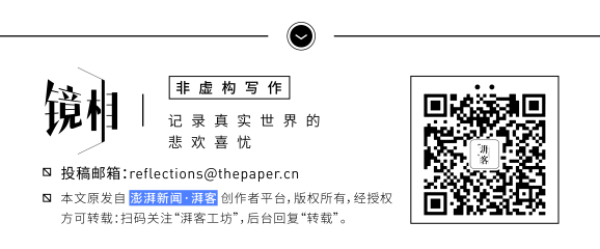十八年里,“天地”不曾缺席我生命
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象征着一场新的轮回。在漫长的人生里,是这样顺应着节气、天文变化的历时里的节日昭示着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在中国传统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依托把人与人联结起来,因而在纷乱流离的生活里,人在时空中始终有一个确定的坐标,通过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镜相联合北大传播学课程的作者们,共同书写家族历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视角的转换,折射出几代人沟通、理解和凝视。是在代际轮回里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与情感,故土与新人,赋予了中国人“家”的精神归属。
在德宏地区,汉族百姓堂屋正中的位置大多供奉“天地”(或称“家堂”)。一般分为三堂,正堂为五福堂,供奉“天、地、国、亲、师”,左堂为奏善堂;右堂为流芳堂,供奉宗族德传百世,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这样的天地一般为三组木制牌坊,组成左、中、右三堂壁龛,供奉天地。
在我前十八年的生命中,“天地”始终未曾缺席。
一:见“天地”

老家堂屋的正墙面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天地始终铺陈在老家黑漆漆的堂屋的正墙面上,红底的板上镌刻着许多看不懂的文字,案前的烛光和香烟似乎终年不断。每当过年回老家时,大人们都会围绕着天地忙前忙后,而我和兄弟姐妹们也要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天地面前磕个头,并在心里默念一个小小的愿望,而此时公公嘴里也会念念有词,无非是“列祖列宗保佑:全家健康平安,后辈工作顺利,小辈考上大学”之类的祝颂语。
但是在我和天地正面相遇之前,它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过于模糊以至于有些神秘的意象。没有大人向我介绍过它的功用、来历甚至准确的称谓,繁体字和过于简省的文言使我无法读懂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而仅能依稀辨明的“天”、“地”、“位”几个字反而为其增添了更多神秘,再加上其本身所具有的迷信色彩,天地在我眼中甚至是恐怖的。我无从知道它在我的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只知道对它的祭拜会在每次回老家过年时固定上演,同时伴随着一系列细致、繁琐的习俗和规定。
两年前,我们搬入新家,在听到公公奶奶面对我家墙壁的指点以及爸爸妈妈之间窃窃私语式的争执之后,我逐渐意识到,天地不再是一个只存在于老家堂屋中的东西,而是马上将会进入新家,与我的生活正面相遇。
但是我的内心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排斥的。首先由于新家空间有限,唯一可以陈设天地的地方只剩下了钢琴上部的墙面,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笨重的陈设将破坏新家原有的装修风格并使之不再协调。此外,我更为深刻的不满在于,作为一个已经接受教育多年的高中生,我对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生活中的封建迷信习俗其实是充满不屑的,而天地在我看来无疑就是封建迷信的代表之一。这让我无法想象我必须作为家族的继承者继承对天地的祭拜,承袭那些繁琐并且陌生的习俗。
而我的妈妈同样认为天地不过是封建迷信的遗留物,现代人的生活中早就不应该保留其和与之相关的繁琐习俗,于是我、妈妈用争吵向爸爸表示了强烈的反抗。由于安装天地是公公一直以来的坚持,爸爸不便违抗,所以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无奈演变为最后的烦躁和激动,并最终以对我“只会读书,不会孝敬公公奶奶”的指控结束了这场争吵。
几天后,天地还是被安装上了那面墙壁,即使使用了更为精致和昂贵的木材使它变得略微美观了,它还是和整个新家的风格格格不入。
如今快两年时光过去,我一直在思考我应该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放置天地及其背后的文化。虽然我还是不能相信其能够沟通此世与彼岸,但是在一次次目睹曾经在农村老家才会上演的习俗被复制到我城市里的新家以后,在全家人借此机会团聚了数次以后,我忽然找回了久违的家族式生活的感觉,感受到了一种名为“传承”的体验。我开始接受天地在我生活中的存在,开始不再对其扁平化地看待,而是体会其所承载的关于民族文化、关于家庭和家族关系的深刻内涵。
二:汉民族文化作为异质文化

德宏佛教建筑
我出生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五个世居少数民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据全州人口的52%,少数民族文化塑造了德宏文化的气质,并以各种民族节日、民族艺术不断彰显和强调。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化更是被当作德宏州旅游业发展和文化形象宣传的重点,被推广至城市形象设计、对外宣传工作中。并且因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人口最多,所以拥有较为浓厚的佛教宗教氛围,佛寺、佛塔、奘房等建筑随处可见。
历史上德宏属于傣王国“哀牢国”,直至明朝设宣抚司、分封傣族“土司”才正式确立了中央对德宏的管辖。
德宏汉族的来源主要包括:明朝三征麓川时,少数随军而来留下的汉民;明清之际,在此屯田的屯兵戍卒;到缅甸挖矿寻宝的商人;解放后响应国家政策前来建设边疆的内地人民。由此可见,德宏汉民族大多由外迁移而来,并非本地世居民族,这就意味着汉族虽然是仅次于傣族、景颇族的德宏州第三大民族,但是面对历史悠久、影响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文化,汉民族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注定是外来的、异质的。
汉民族文化过于短暂的历史加之强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使得德宏缺少汉民族文化繁衍的土壤,再加上德宏位于中国最西南部边疆,长期属于“南蛮荒芜之地”,缺少内地儒家文化、宗族文化的辐射和教化,难以形成较为完整、成体系的汉民族文化。这意味着,不同于宗族文化昌盛的东南沿海地区,祠堂、牌坊等代表宗族文化的文化符号在德宏几乎难觅踪迹,大部分汉族人家族史短暂,并且因解放前德宏长期处于战乱,故祖坟遗失、不知祖籍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此外,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之后,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傣族佛教文化极强的影响力和统摄力使得汉族文化被严重同化,傣族原始宗教以及佛教形成垄断,几乎主导了包括汉民族在内德宏州大多数人民的宗教生活。
然而,“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民族更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寻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天性,即使缺少宗族文化的传统和土壤,德宏汉民族依然保留了对寻根追源、维系宗族的坚持。于是,家庭作为一个更小的单位成为了德宏汉民族宗族文化的依托和载体,祠堂、牌坊浓缩和简化为天地、家谱等更为家庭化的符号,德宏汉族人民也就找到了更适应于边地地域和文化情况的宗族文化形式。
三:从家族到家庭

家族合影
本省陈姓支系繁多,历史久远,来源复杂,几经周折移居多地,为此我家原籍家谱身庚墓地记录等早已佚失,自老祖以上族史都不可考。
近年来重修家谱,经家中长辈多方寻觅考证,才模糊得知我家祖籍腾冲,后经辗转移居龙陵县,老祖的父亲由于贸易关系移居缅甸,娶妻生下老祖陈小学,后老祖父亲因贸易在缅甸邦弄山被强盗所害,无葬身之地,很快老祖母亲也不幸亡故。父母双亡的老祖幸遇一自中国赴缅甸贸易的匡姓人家收留,后带回中国,经好心人介绍到老家上东村入赘匡门,与匡氏长女定秀成婚,并取名匡陈学。按照传统习惯,凡是招婿之姓,三代后归宗,故我家现已恢复原姓陈姓,但天地牌左侧流芳堂上却依然镌刻着“徴音颍川郡匡陈氏门”的文字。
老祖与祖太共育有五子三女,公公排行第三。据公公所说,幼时他和所有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老家,过着“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屋”的大家庭生活,彼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物质十分匮乏,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没有一粒米,麦糠就着菜叶子煮粥吃就能糊弄一顿,饭菜没有一滴油,不到两小时肚子就饿了,只能到山里找野菜充饥。公公和叔公、姑太们成人以后就各自分家,公公与邻村的奶奶成婚后继续住在老屋赡养老祖和祖太。
公公从小没有读过书,只在当年“社教”时上过三个月的培训班,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没有电灯,只有点着“火油灯”学习。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勤奋学习,成了村里的“识字人”,被抽调到农村工作队,随后进入农村信用社工作,由此撑起了一个家。
公公奶奶共生育有两女三子,爸爸是家中长子。起初爸爸在镇里初中读书,但是中考成绩并不理想,公公对子女教育很是重视,于是支持爸爸到德宏州最好的初中“补习”一年。一年的静心学习后,爸爸中考成绩突飞猛进,考入省级重点专业学校修习汽车修理专业。1995年毕业后回乡,在当时的国营汽车修理厂工作一段时间后,转而到市属职业技术学校工作,教授汽车修理。也正是这个选择让爸爸免于经历几年后的下岗潮。
我的妈妈是团坡村人,家中赤贫,全凭舅爹成人后辛苦供养才得以读完初中,由于妈妈自小聪慧,学习刻苦,中考取得优异成绩,无奈家中条件艰苦,妈妈只能选择报考毕业后“包分配”,并且离家近的师范院校。从师范毕业后,遵循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妈妈被分配至团坡村小学教授语文,并在实习期间与爸爸相识并成家。
我出生后,乡村式的家族生活模式已经被城市核心家庭生活模式所取代,支撑宗族文化的家族式生活实际已经不再存在,新一代不再具有家族式生活的体验和经历,加之复杂繁琐的习俗不断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导致原本就较为薄弱的汉民族文化传统进一步缺失,边地汉族宗族传统的维系变得更为困难。
于是,当宗族文化难以为继时,“天地”作为宗族文化简化的物质载体,从大家族流入小家庭中,承载了当代德宏汉族人民对传统宗族文化的追思和继承。
四:重识“天地”
我于是开始重新正式地体认天地。

德宏宗教建筑
家谱记载:天地正中央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神位,天指老天爷,地指土地爷,国即代表国家,亲指代父母、祖宗,师指老师,合称“五圣”,是我国古代民间供奉的“神”。
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天地国(君)亲师”五个字的书写也很有讲究。“天不连二”,指“天”字里面的“人”不能顶着“天”字的第一横,因为中国古代以天为至上神;“地不离土”,指“地”字的“也”与“土”旁写成连笔,不能断开,意为地由土构成,人类的一切生存所需,都取之于地;“君不开口”,指“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须封严,不能留口,谓君王一言九鼎,不能乱开;“亲不闭目”,指“亲”(親)字的目字不能封严,否则子孙不肖,父母死不瞑目;“师脚要直”,指“师”的竖笔一定要直,否则歪脚老师教不出好学生;“位不离人”,指“位”字的“人”部与“立”字要相连,且字形端正稳固,即为人须端正,不能越位。总之,“天地国(君)亲师”五字寄托了汉民族对原始崇敬和信仰的延续,对家庭和睦、生活美满的朴素愿景以及对孝亲敬长、尊师重道的传统礼教的坚持。
由此,我便不再单纯地将天地当作腐朽的文化糟粕,而是终于体会到了天地所蕴含的厚重历史和时代变迁的痕迹。作为“外来客”的德宏汉族先民大多居住在城镇周边的山间,破碎的地形阻碍了宗族之间完整联系的形成,薄弱的汉文化土壤和德宏地区落后的物质条件使得修葺祠堂、建立宗派等传统的宗族组织方式不再现实。于是,天地作为被保留下来的宗族文化形式,寄托了边地汉民族皈依、传承传统宗族文化的心愿,与之相关的各种礼俗则作为一种“仪式化的传播”,成为构建宗族间文化共识、强化心灵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过程。
我终于明白,为何还算个文化人的公公要一辈子重视和强调传统宗族文化的传承,坚持在过年时主持“接王”、“送王”等繁琐礼节,并要求下一代也要在宅屋中陈设天地以供祭拜,并不完全是因为他迂腐陈旧、信奉封建迷信,而是出于对原有家族式生活方式以及那种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彼此支撑的安全感的追忆,使他在“家族”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今天,依旧希望各自组成小家庭的儿女们能够继续将“家族”作为永存的共同体来看待,能够继续保有互相支持、同心协力的美德。
终于,天地在我眼中不再是神秘、恐怖的未知物,我渐渐接受了它在我生命中的存在,也渐渐增强了对自己汉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及滋养自己的汉民族文化的理解。
五:搬迁
二〇一六年腊月,为响应国家扶贫搬迁“应搬尽搬”的政策号召,我家彻底从居住了九十四年整的上东村搬迁至法帕镇,一年后,老屋拆除。
老屋的倒塌意味着又一个维系和承载家族的实体消失了,家族被正式拆解为数个家庭,也意味着家族的百年历史彻底地被尘封进了薄薄的家谱里。
但是,天地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公公的坚持下,家族的每一个小家庭都陈设了天地,而那些仪式性的习俗同样被承袭了下来。每当过年时,各家依然会轮流请客,小家庭再次以节日的名义短暂地聚合为大家族,围绕着天地所展开的一系列习俗在公公奶奶的指挥下再次有条不紊地开展,而小辈们依旧像在老家一样,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天地面前轮流跪拜,同时聆听着公公默念的祈福。
尽管在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我们眼中,天地早已被高度祛魅了,它更多地是一种符号和精神,繁琐的习俗也被适当简化。但是我们却不再会质疑和排斥天地的存在,作为流散在边地的陈姓支系,这是少数能提示我们和祖先关系的事物,同样,作为生活在现代文化中的个体,这也是不多的能够让我们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方式。所以我愿意将其称为一个边地汉族家庭对宗族文化的皈依和传承。
六:尾声
一百年以来,中国无疑进入了一个高度流动的时代,“安土重迁”的规则被彻底打破,乡愁变得廉价,而迁徙成为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对乡村的蚕食意味着乡土社会的逐渐远去,传统的来自家族和家乡的牵引力也因移动通讯和现代交通的发达而逐渐式微。无数像我一样的新一代青年无法理解陈旧复杂的宗族文化,并将其粗暴地归结为封建腐朽文化的残余,同时对于家族抱有十分有限的共同感。
但是,家族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存续和组织的方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却不应该被我们抛弃,虽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家族式的生活状态以及全面继承宗族文化已经不再现实,我们依然可以以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式对宗族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并且保留家风、家教等优良传统。
虽然在高度现代化和利己主义的城市,家族和宗族无疑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及少子化的趋势意味着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将永远地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退场。但是我们仍不可否认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羁绊依然是无比真实的,这种发端于血缘又联结于亲情的情感是不会随着乡土社会的远去而消弭的。尽管家族高度分化为家庭,我们仍会本能地渴望团圆、渴望在患难时得到来自家族的扶持,渴望在荣耀时得到家族的承认,这种来自乡土社会的感召将会永远埋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成为民族的精神基因而永存。